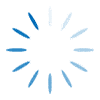仰春能感觉到高热正一点点从骨缝里退去,鼻息间的灼烫感渐渐平息,身上的酸痛也如潮水般退去,四肢重新攒起了力气。
看来喻续断的诊断和治法并无差错。
只是——
仰春抬眼看向在烛火下给银针清洗消毒的喻续断,心中五味陈杂。
爽是真爽,尴尬也是真尴尬。
喻续断察觉到她的目光,偏过头来,语调平淡如旧:“还有哪里不适?”
仰春的声音细若蚊蚋,“舒服多了。”
那人轻轻地发出一声气音,好像是在笑,只是极短,快得让人疑心是错觉。
“舒服了就好。”
那股想把自己裹进被子里的窘迫又翻涌上来,仰春连忙侧过身面朝床里,心里暗诽:你说的 “舒服”,最好指的是病情。
喻续断将银针一一收进布袋,淡淡嘱咐:“这几日饮食清淡些,今夜回去发发汗,多饮温水,少碰茶盏,三两日便能大安。”
仰春闷闷应着:“哦,晓得了。”
那人没再回答,只听木门‘吱嘎’一声,显然他已准备要走。
仰春听见门响下意识地回头看。
却见那人漫不经心地撩动着还有一片暗色的衣摆,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院外静默的三道人影中的一道,几不可察地顿了顿。
“勿纵欲,远男色,遵医嘱,方得愈。”
仰春喉头一哽,竟说不出话来。
喻续断步子不快,却迈得沉稳,没几步便消失在院门外。
仰春望着空荡荡的门口,只觉今日种种皆模模糊糊,令人不知所措。
且高潮之后身心不知道是疲倦还是放松,困顿得很,只想蒙住被子好好地睡。
于是她扬声朝院子喊道:“芰荷,进来收拾,咱们回府。”
芰荷连忙应着,小碎步跑进门时,忍不住回首小心翼翼地偷瞄了一眼林衔青。
无他,自打仰春晕厥后,他们虽守在屋外,里头的动静却一丝不落全听进了耳里 ——那娇媚婉转的轻啼,声声入耳,缠得人耳根发烫。
芰荷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林衔青的面色有多难看了。
只觉得他中毒失血剜腐肉都没有此刻面容苍白。
不过二小姐好意救他,他还害得二小姐中毒,芰荷心里有一些不满。
她不再理会,走进屋子,为仰春擦拭干净后,径直进屋伺候仰春擦身换衣,扶着人上了马车。
高飞见仰春轻声细语嘱咐了一句“照顾好你家小将军,快将人抬进去别受凉了”之后,施施然越行越远,不由纠结地挠挠头。
他见林衔青仍旧泡在热水桶里,便决定按照柳姑娘的吩咐再将小将军抬回去。
手臂刚刚环住水桶,就见林衔青‘哗啦’一声从水里站起身,长腿一迈,跨出桶去。水珠顺着紧实的肌理往下淌,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声响。
高飞急忙伸手去扶,“小将军,你要去哪里?”
林衔青面色阴沉,下颌线绷得死紧,面色像有墨汁滴出。
他拂掉高飞的手臂,冷声吩咐道:“再去寻别的大夫来。”
*
仰春的书铺修葺已近尾声,乌木书架沿着墙根顶天立地地立得笔直,隔出的区域用素纱、青绫、月白杭绸细细垂挂,风一吹便漾起层层迭迭的涟漪。
李掌柜和木生按仰春的嘱咐,将书卷分门别类码上书架,经史子集按部就班码得齐整,连话本传奇都按朝代归了类,满满当当的书脊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二楼的梨花木长桌皆已就位,李掌柜搬来半箱花色各异的桌布让仰春挑选,她指尖拂过绣着兰草的湖蓝锦缎,最终敲定了几款花色风格各有特色的料子,着人细细铺展上去。
接下来便是里头的陈设摆件,这需得极高的审美来打磨细节。
仰春深知自己现代的审美不足以撑起文人雅士常来的书铺,便决意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,托人请来了姑苏城知名的造景师傅。
老师傅递上名帖时说,是他操刀了 “醉仙楼” 的装潢。
仰春指尖捏着名帖,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临江飞阁的奢华典雅,檐角风铃叮咚,还有个总爱慢悠悠抛接银色小刀的懒散身影,刀光映着他眼底的漫不经心,倒比醉仙楼里的景色更令人印象深刻。
她望着窗外偶有吹来的清爽的风,心里琢磨着:这些天过去了,不知道那位总爱抛刀子的主儿,把传薪坊的地契理顺了没有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