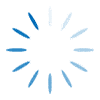滞留的时间有些长了。
齐鹭是被刺目的阳光惊醒的。
她勉强睁开眼,视线模糊不清,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。
不知为何身体像是灌了铅般,脑袋沉甸甸的,明明已经醒了,却还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向昏沉的深渊。试图撑起身体,手臂却软绵绵的使不上力,手肘一滑,整个人又跌回凌乱的被褥里。
额前的碎发被汗浸湿,黏在红润的脸颊上。昨晚的记忆断断续续地浮现——陆瞻白起了次身,温暖的胸膛骤然抽离令她不由地拽住了他。
再然后手被温柔地轻抚开,在轻声细语的问询下,他拿着水杯抵着她的唇喂了点水。
接着就是完全失去意识的沉眠。
窗外传来鸟鸣声,清脆得刺耳。她眯起眼看向墙上的挂钟——指针已经逼近十二点,远远超过了平时起床的时间。
身侧的床单也早已从人体的温度冷却。
不安感逐渐升腾,抓起手机一看——果然有好多个来自季非虞的未接来电,可是她前一天交代过了去朋友家玩。
就说玩太晚了,应该没事吧?
匆匆整理好衣服准备离开,途经楼梯拐口时却迎面撞到正要上楼的齐槐,男孩亮亮的眸子盛满期待,邀着齐鹭往餐厅去。
她有点尴尬,但男孩没注意到,还很欢迎她的拜访。
在那是系着围裙的陆瞻白,与一桌丰盛的午饭。
“我正让小槐去叫你呢,睡醒了来吃饭吧。”温润的眉目一刻不离她,“你也好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了呢。”
为了不沾上油污,他的头发用木簪全部盘在脑后,没有很刻意装扮,倒颇具人夫风情。
饭菜的香气四溢,正好勾起她的饥饿感,她想也不差吃顿饭的时间。
陆瞻白自然地坐在了她的对面,齐槐却不坐在他旁边,反而挨着她落座。
他做的饭很好吃,季非虞的厨艺也不错。如果把陆瞻白与季非虞两人做比较的话,反而是季非虞更喜欢做些精致的菜肴,陆瞻白的饭菜更具有锅气,毕竟他在乡下长大,从小就做一家人的菜了。
心下默默对比间,碗里就多了齐槐夹来的一只鸡腿,她没想到小孩会主动夹菜给自己,而她什么表示也没有真是臊得慌,便又给他夹了回去,叮嘱他才要多吃点长身体。
细细瞧他一眼,才发现齐槐瘦弱得过分,真有些营养不良。
按理来说不应该啊,陆瞻白这么有钱,难道这孩子挑食吗?
于是也就这么交代了陆瞻白一句,得来他欣慰的一眼,表示他会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健康的。
有病……这是需要她来提醒的吗?又不是她的孩子,这种貌似期盼妻子顾家的神情莫名让人火大。
最终这顿饭还是平静地结束了,如果忽略后续两边不停夹菜的话。
本来都要换鞋离开了,一双小手却拉住了她的衣角。
“姑姑,再玩会好不好?”
期期艾艾的目光投来,齐槐仰着脸,睫毛扑闪得像蝴蝶的翅膀,“我最近学会《致爱丽丝》了,我想弹给姑姑听。”
他踮着脚,细软的手指紧紧攥住她的衣角,丝绸布料在他掌心皱成一朵小小的花。
齐鹭低头看他时,他立刻松开衣角,转而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住她的手腕。指尖凉得像玉,轻轻晃着她的手臂问道:“就听一小段,好不好?” 声音又软又糯,带着点可怜巴巴的颤音。
“好啊,小槐可真厉害。”反正只是孩童的一个小小请求罢了。
男孩纤细的指尖落在琴键上时,像是一簇雪落在黑檀木上。他瘦弱的身躯微微前倾,脊椎的骨节透过丝质白衬衫隐约可见。似有柔和日光笼罩着他,为柔软的黑发镀上金边,发尾随着演奏的节奏轻晃,如同天使垂落的羽翼。
回旋曲式的旋律每次回归时都更显缠绵。
琴声流淌间,他忍不住侧头偷看坐在一旁的齐鹭。镜面般的钢琴漆映出他们相似的侧脸线条:同样微微下垂的眼尾,同样在思考时会不自觉轻咬的下唇。他注意到齐鹭今天也把头发别在耳后,露出和自己如出一辙的、略显尖削的耳廓。
尽管父亲时常说他与母亲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,但血脉的联系还是能轻易让他找到他与她的相似点,透过骨肉传递,细细密密融入血液与每一处神经。
他是这世上唯一与她血脉相连的人了,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像呢?
这个认知让他心头涌起奇异的喜悦,但不妙的是紧接着第35小节的颤音处失误了——就算是大人既专注演奏,同时又分神偷看他人也会出错的。
幸好曲调未变得怪异,他继续着这首纯真而温柔的献礼,如同作曲家将旋律献给心上人一般,他将笨拙的演奏献给最在意的“姑姑”。
想靠近却又不敢明言,只能委婉地致以爱丽丝,致以唯一的人。
临近尾声,没有表现完美的挫败感萦绕心头,齐槐的睫毛慌乱地颤了颤,眼底浮起一层湿润的光。
最后一个和弦余韵未散,他已经跳下琴凳扑过来,一头扎进她怀里:“姑姑我有的地方弹错了,对不起。”呼吸急促,心跳快得透过单薄的衬衣传到她手背上,像揣了只受惊的雀儿。
齐鹭摸到他后颈细密的汗珠,才发觉这孩子紧张得浑身发抖。
弹错的琴音也只是一刹那的违和,对于她这种音痴来说更谈不上影响了。
似乎没有什么可逗留的理由了。
姑姑,再听一首,就一首——
他坐回琴凳,想这么说,嘴唇无意识地张开又合上,但最终还是咽下了这无理取闹的请求。
“……妈妈。”??某个藏在心底太久的词,在这个慌乱的瞬间,突然挣脱了束缚。
这个音节轻得几乎听不见,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凝固了。
齐鹭正要起身的动作顿住了。她回过头,看见男孩死死低着头,睫毛剧烈颤抖着,在苍白的脸颊上投下破碎的阴影。他的手指攥紧了琴凳边缘,指节泛出青白,仿佛要把那个脱口而出的词硬生生按回去。
“别走,妈妈……”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,却又倔强地抿住嘴唇,把后半句话咬碎了咽下去。
齐鹭蹲下身来。
她的手掌贴上男孩的脸颊时,感受到了一滴温热的湿润。男孩下意识想躲,却被她轻轻捧住了脸。
“没关系的。”她的拇指擦过他的眼角,声音比平时软了八度,“你想妈妈了对吗?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了,但她会一直看着你,爱着你的。”
齐槐的瞳孔微微扩大,像是没听懂这句话。他的呼吸变得又浅又快,胸口剧烈起伏着,仿佛随时会哭出来,又仿佛在拼命忍耐着什么。
忽然被搂进了怀里,他的身体僵硬了一瞬,随后彻底软下来,额头抵在她的肩膀上,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衣摆,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。
“真的吗?”他的声音闷在她的衣料里,“会一直看着我,爱着我吗?”
齐鹭摸了摸他的后脑勺,发丝柔软得像雏鸟的绒毛。
“嗯。会的。”
“母亲都会爱着她的孩子的。”
他是懂事的孩子,没一会就情绪稳定下来了。她与他告别,他又回到只有他与父亲在的家。
下一次再弹钢琴给她听是什么时候呢?还有这样的机会吗?
视线随之转移到钢琴上,《致爱丽丝》的乐谱被风吹动,哗啦啦翻过几页,最终停在了他弹错的段落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